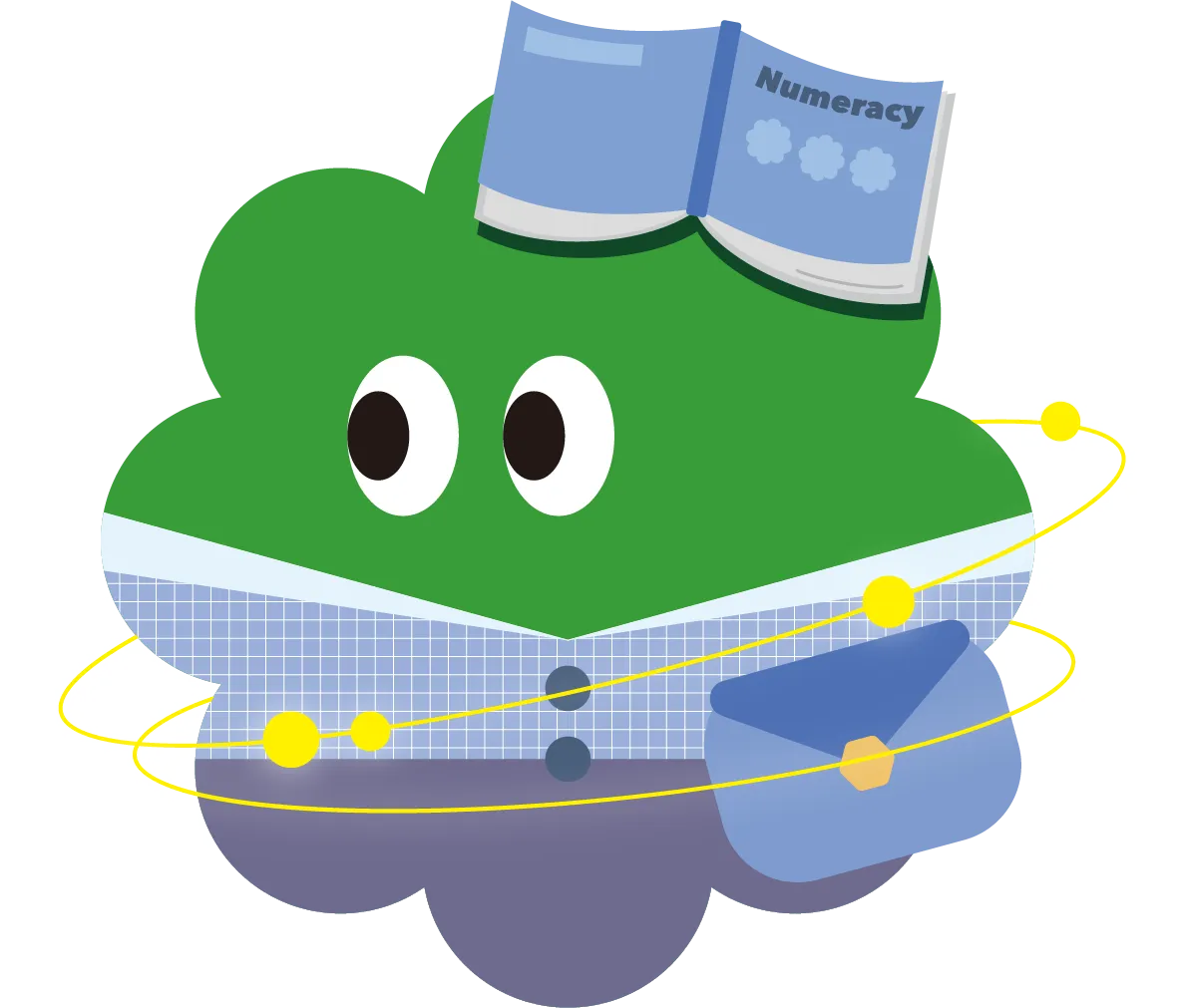作者 曾子薰
有一天,我發現我的貓有點怪。
不是感覺,而是確知哪裡不太對勁。小米是隻白底黑斑的貓,一雙墨黑大眼閃爍著惹人喜愛的光芒,多麼無害純真的小動物。我的小米像天生穿著乳牛裝,舔拭自己皮毛時唇齒間彷彿會溢滿奶香,好甜,好乖。
──我懷疑小米誘拐了一隻黑貓回家,然後逃獄似地跳窗輕盈離開,否則要怎麼解釋這隻黑糖凍一樣烏漆麻黑看不見一點白色的貓。牠怎麼可能是我半年前在樓下撿到的小貓,然而,藍色項圈上確實寫著我的名字及這裡的地址。
到底是怎麼做到的?我的小米不是我的小米,儘管牠湊在我臉頰旁蹭呀蹭的感覺跟以前一模一樣,但我就是覺得彆扭,還特別毛骨悚然,也許更多的是不敢置信……這種鬼片般的情節居然發生在我這麼普通的一個社會新鮮人身上,但一切都還沒結束。
當我那火鶴圖案的收納盒變成天鵝圖案、鬧鐘從粉紅色變成藍色時,房間原有的配置已經被未知的力量破壞了大半。我從一開始的歇斯底里到現在只剩微弱的不安已經過了兩個多月,傾訴過煩惱的朋友愉快地得知我總算從幻想中脫離,紛紛前來慰問。
「你終於放棄這個奇怪的社會實驗啦。」朋友如是說,聽了這話的我又自閉起來,恐怕事情沒有真的發生在他們身上,這些社會化完全的僵化腦袋是無法感同身受的。
親近的人都把我當瘋子,像教授這樣的權威人物更是對我敬謝不敏。我以前念哲學的,忍不住把我這段時間的困擾傾訴給大學時熟悉的教授知道,教授很努力地憋住,最後還是大笑著說:「這可能就是尼采發瘋前遇到的事。」從此我沒再找過他。
我就是在這種走投無路、只能獨自到圖書館查資料解釋身邊異常的情況下,遇到那個男人的。
男人的長相,我已經記不清了,不如說,在他離開後,這點印象便在我腦海中消失殆盡,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卻記不住臉孔的男人,讓我不禁覺得又有超脫科學的解釋。
男人的第一句話就是:「我在上一個時空也見過妳這個樣子,像要把整個圖書館都翻遍一樣。」他盯著眼神有如發現新大陸的我,說:「我請妳喝個下午茶吧?」
請別譴責我淺薄的自我保護意識,但我確實沒思考多久就跟著他走了。我們坐在咖啡廳,假日的街道上人流依舊熙熙攘攘,城市的步調著急而緊張,我不禁好奇,這之中會不會有人跟我有同樣的困擾。
還沒等飲料上桌,男人就開口說道:「本來我還不太清楚,現在看到這個時空的妳也遇到一樣的困擾後,我幾乎可以確定,妳和另一個時空的妳的房間,剛好落在蟲洞連接的兩端點上。」
他自顧自說了一大堆,才突然想起什麼,「啊……抱歉,我忘了自我介紹,我是十年後的時間旅行計畫志願者,對這種事情稍微比較了解一點。」
我不禁失笑,怎麼會有人這樣做自我介紹?
「時空旅人先生你好,既然如此,我就是平行時空小姐,就麻煩你今天幫我解惑了。」
男人好像跟不上我的幽默,也可能是他沉浸在他的思維裡沒聽到我說了些什麼,「……你大學念哲學系?」良久,他終於道。
我只是苦笑,已經沒有什麼事情能嚇得到我,「你連這個都知道啊,現在可以解釋一下什麼蟲洞啊平行時空之類的東西了嗎?」
男人點點頭,「我是數學系,你好。」然後他偏頭想了想,像在思索一個我能理解的解釋,「大概就像,如果你以前唸過認知哲學,那你應該聽過『孿生地球思想實驗』,你可以試著想想看。」
我當然聽過孿生地球思想實驗,普特南假設宇宙間存在有一顆跟地球完全一模一樣的星球,我們稱它為『孿生地球』,兩個星球高度相似,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「水」。在孿生地球上,「水」的分子組成是XYZ,除此之外就跟地球上的「水」一模一樣。
因此,當孿生地球上的居民講到「水」時,他們心中浮現的事物,跟地球居民講到「水」時,應該是沒有差別的。即便如此,這兩個星球上的居民提到的實際上是不同的事物,所以它們的意義應該是不同的。
但這跟現況又有什麼關係?我皺起眉頭,用表情傳達我的不理解。
「跟那個實驗剛好相反,妳跟另一個時空的妳的房間,裡頭的物品本質是相同的,卻有外在的差異,這種差異實際上源於妳們不同的內在,去決定了妳們會如何布置自己的房間,又是如何不適應另一個自己布置的房間。」他解釋道。
這是我畢業後第一次深入思考只存在大學課堂上的論證。我想起思想實驗裡的孿生地球居民其實沒有分子的概念,也依然有不知道水之組成的地球居民,是否是相同的事物是由認知上的差異而定的嗎?這樣的說法可以適用在超自然的現實上嗎?
男人拍了拍手,喚回我在宇宙中漂流的思緒,「稍微有概念之後,現在我用我的專業科目跟妳解釋看看我的想法。」
「妳知道拋物線吧,實際上,蟲洞在人們的假說中就像一個拋物線。」他用手指沾了沾水杯裡的水,在桌上畫了一個拋物線的圖形,「拋物線之所以會叫拋物線當然是有原因的。我不認為蟲洞連接的所謂『白洞』和『黑洞』是一方只吞噬而一方只吸收,我傾向作用是互相的,得到一部份,必然也失去原先的一部份,這是我所假設的。」
「而妳們的房間正好就落上這個蟲洞之上,妳們是對稱的兩個點,在數學上稱為『共軛』,以共軛複數的例子來說,實數就是事物的本質,而互為相反數的虛數便是這些外表的不同之處。」
我沉吟了一陣,「也就是說,既然不同的地方是相反數,那麼,我對另一個我的審美產生極端的排斥是理所當然的。」
「妳關注的點很奇怪,不過妳說的對。」男人終於笑了,「真不愧是哲學系的,一點就通。」
那天過後,我就沒再見過男人──或許有,只是我再記不起他的外表──卻倒是對房間的變化心安不少,不再每個早上都擔心少了什麼東西,儘管難以理解,但在找到一個似乎合理的解釋後,便覺得這一切是新奇大於恐懼。
我時不時買些新的小東西回來,等它有一天變成另一個樣子,也成為一種異樣的生活樂趣。然而,在習慣了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的生活後,某天早晨,我再醒來時,竟恍然像回到了好幾個月前。
整個房間的擺設都像以前那樣,沒有改變。
我的直覺告訴我,是我的東西都回來了,再多想一陣,我卻突然無法確定──是不是我已經不在我原來的時空了?
我盯著書櫃上休息的小米發呆,花色是許久不見的白底黑斑,懷念的同時也感到一絲悵然若失。我似乎已經開始習慣另一個我的生活,而在我習慣了那一切之後,我還算不算得上是原來的我呢?
我很在意,究竟是我也來到了另一個時空,還是一切都回到原來的時空了?這個世界的我跟另一個世界的我還是同樣的一個人嗎?
位於同一條線上,就算是對稱的兩點,所帶有的性質也不盡相同。
立足於似同非同的生活環境中,我不知道若是我離開了自己的時空,對這兩個世界來說,算不算失去了什麼或得到了什麼。
我又在假日上圖書館尋求解答,我驀然想起那個從此沒了蹤跡的神祕男人。我看向外頭,繁雜的人潮間,或許那個男人亦身在其中,若是看見窗邊苦惱的我,他還會為此駐足嗎?會不會這裡也有不同時空的他?我們還會再次相遇嗎? 然而,這次我也明白,這些問題或許注定再也找不到答案,他大概早已離開這個時間點的時空維度,從人群間擦肩告別後便是永別,短暫地交會後就此平行,脫離現實常軌的假想終究只是假想,沒有人能證明孿生地球的存在,正如沒有人能證明另一個時空裡孿生的我,一切彷彿只是我腦海裡的一場風暴,捲著這段時間的不安、好奇與其他一切沒入未知的蟲洞之中,再也找不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