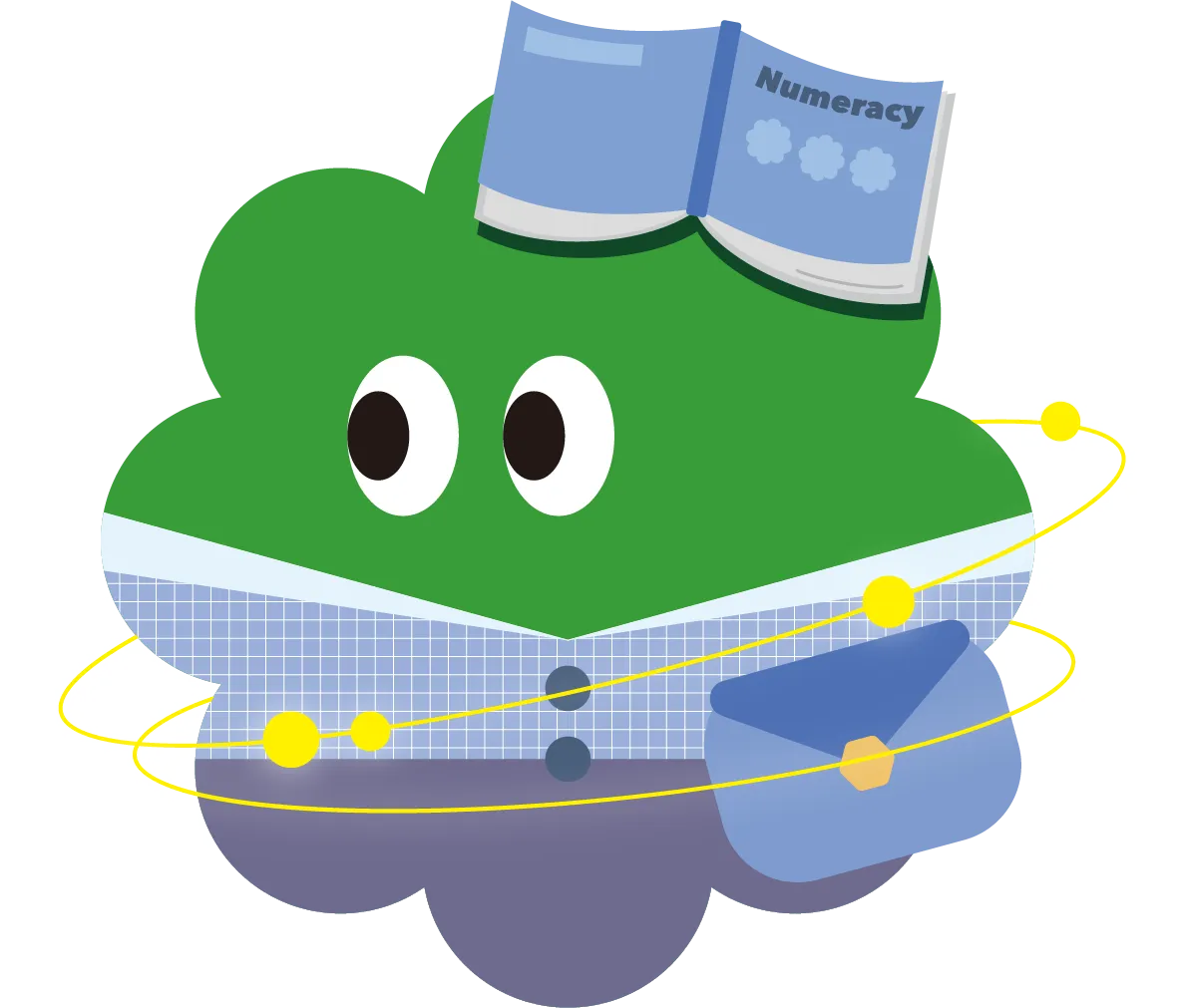作者 盧品臻
你總是說我的世界是由1和0組成的。
我說你的生活是由2構成的。
「那是你的模範生獎狀?還是比賽得名的?」你躺在那小小的單人床上這麼問著。
你的語氣讓我感到不怎麼舒服。就像那些在學校的人,他們眼中的我跟他們不同,這種感覺是我無法形容的厭惡感。
「怎麼了嗎?」即便心中不悅,但我還是以平和的口氣問道。
「沒什麼,」他看著天花板說:「只是覺得你的遭遇有點可憐。」
「什麼意思?」
「你會不會覺得有時候自己活得不像一個人?」他轉頭看向我,說:「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就像一台電腦?總是依照他人的想法去執行?」
聽到他這樣說,我想起我站在台上領獎,我面對他們的目光。在他們的視線下,我感覺我是赤裸地站在他們的眼前,不安充斥在我心中的每一處。
下了頒獎台,我想回到同學身邊,我卻無法辦到──我跟他們不同,我背負的期待更多,我必須更完美,不能辜負旁人的期望。
必須表現得像一台精密的機器、一台電腦。
你打開 FL Studio 20,點開你昨夜編輯完的檔案。左半部是編輯大鼓、小鼓等樂器的小視窗,右半部則是軌道,上面放著你花了數日所努力出來的結果。
「聽聽這旋律。不錯吧! 我可是花了很久時間在點擊這些音符。」
這首曲子比往常多了很多層次,像一層一層的積木堆疊出一座層樓疊榭的建築。
「你比以前熟練了。這很好聽。」
笑容在你臉上暈開。
此時我腦中忽然浮現一個想法。
「2的n次方。」
「你說什麼?」你轉過身來,你一定對我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充滿疑惑。
「我說,你的生活都是2的n次方。」
你皺了眉頭,但很快又擺出一副無言的表情然後繼續混音。
「你這是在記仇嗎?電腦先生?」他無奈地問。
我假裝不知道,回了他:「什麼?我不明白你說什麼。」
但我很清楚,你說我像一台二進位法的電腦,我也只能說你是一個音樂作曲工作狂。至於2的n次方,就我所知,二分音符、四分音符那些拍子,都與2的n次方密不可分。
其實我也不是刻意諷刺你,我總是覺得你把自己逼得太緊了。
我看得出來,你其實是個很內向、害羞的人,但同學們總會要求你幫忙播派對上的音樂,讓你在全班面前彈琴,甚至是在全校面前幫忙伴奏。你一定不喜歡這樣,但即便旁人看得出來,他們總是忽視。
可是,你總是強裝微笑,努力達成他們的願望,追求他們心中賦予你的卓越及完美。就如你現在正在用MacBooks做的事一樣。
「我喜歡創作啊,又沒關係。」你曾這麼跟我說。但你或許不是為了自己的喜悅才這麼拚命。
我知道,你只是希望所有人都好。
有時我甚至會覺得,我們是如此相像。
「你有個弟弟,是嗎?」
我瞬間回過神來,發現自己坐在一個陌生的房間裡。房間內擺了很多書架,還有一張放著電腦的辦公室。眼前坐著一位身穿襯衫和針織外套的女人,年紀大約三十,手上還拿著白色的紀錄板和鋼筆。我從沒看過她。
直到我看到她身後不遠處的書架上擺著戴維.邁爾斯的《社會心理學》和西格蒙德.弗洛伊德的《夢的解析》,我才想起我身在何處。
「你有聽到......」
「抱歉,只是這沙發太舒服,坐到有點忘我。妳剛剛說什麼?」我只能尷尬地笑一笑。
「你有個弟弟是嗎?」
「是的。妳怎麼知道的?」
諮商師笑了笑。「你剛剛跟我說過。」
我這時才發覺,我似乎向眼前的人說出我剛剛回憶的片段。
「你覺得你們之間的關係如何?」
「還不錯。」
「你會怎麼形容你們之間的關係呢?」
我想了想,最後只想到一個答案。
「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關係有三種:重合、交於一點和平行。我想我們之間是平行。」
「為什麼?」
「因為我們之間既相似,卻又是如此不同,」我說:「就像兩條平行的直線一樣,往相同的方向延伸,彼此卻又無共同的一點。」
相同的是,我們都為他人而活;不同的是,你是2,我是1和0。
諮商師笑了笑。「真是有趣的說法。」
「但現在不能這麼說了,因為這個聯立方程式已經不存在了。」
「為什麼?」
我深呼吸,鼓起勇氣。「因為只剩一個方程式了。」
「為何?」
「我的弟弟死了。」
「我很遺憾。」諮商師露出憐憫的表情說:「但你能說說他是怎麼死的嗎?」
「那是在我高中畢業那一年,距離現在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。」
我試著壓抑自己的情緒,努力不讓視線模糊。
「他拿碎玻璃劃破自己的手腕,然後就失血過多,死了。」
我還記得,那時妳躺在一張潔白的純羊毛地毯上,鮮血不斷湧出。我急得哭了出來,用手緊緊按住你的前臂,血還是沿著你的手掌流向指尖,然後滑落,在那片雪白上綻放一朵朵鮮艷的紅花,直到你的生命被那些燦爛奪目的花朵吸取殆盡。
我只能抱著你逐漸冷卻的身軀哭泣,直到有第二人發現你的死訊。
「後來的事,我就記不清了,連他的喪禮辦在哪裡我都不記得了。」
「你和你的家人肯定都不好受。」諮商師似乎想安慰我。
但在她說完那句話後就只是一陣沉默,諮商室內的空氣都變得沉重了起來。
腦海中不停播放那日的畫面,我仍能感受到那時周遭的一切和深刻的心痛,特別是心中的無助感。這讓我的淚水快淹沒了這房間內的一切,直到我無法看見。
有人敲了諮商室的門,打破了寂靜。
「想必是你的父母來了,我得去和他們談一談,等等我就回來。」
然後她就走出那扇門,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。我陷在柔軟的沙發以及無盡的悲痛中。
方才在諮商室裡,諮商師一直都看著她的個案,努力想從他的行為、表情、話語中,拼湊出個案的心理狀況。
她看得出來,個案是沉浸在悲傷中的。尤其是在個案談論弟弟的死時,他雙手交握,手肘壓在膝蓋上,像是他正承受著他負擔不起的事。他甚至隱忍淚水,但諮商師看得出來他可能在心裡放聲哭泣。她開始有點厭惡自己,自己明明是一位心理諮商師卻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個案。
而當個案說到弟弟自殺時,手握得非常用力,所以諮商師的目光便轉移到他的手上,正是那一瞬間,她看到個案的手腕上緊緊貼著幾條免縫膠帶。
「瓊斯先生、瓊斯太太,您好」諮商師客套地打聲招呼。
「我的兒子到底怎麼了?」
個案的父母臉上盡是著急之情,無法冷靜地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。
「您先別著急,」諮商師安撫著瓊斯太太的心情,她說:「我還不清楚為何令郎需要接受諮商,來這裡應該不是他的本意......」
「因為他......」瓊斯太太才剛想說話,卻被瓊斯先生阻止──因為太太已經哽咽到快說不出話來了。所以只能由瓊斯先生向諮商師說明事情緣由。
「上個月,他在他的租屋處自殘,被當天到訪要收房租的房東發現,才立即叫了救護車。幸好傷口不深,也有及時的急救,他才沒有大礙。」
聽了瓊斯先生的這句話,諮商師才發現自己還沒認真仔細地看過病歷。
「但是他再也彈不了琴了。」瓊斯太太突然開口說道:「他彈奏或創作出來的曲子是多麼的好聽......美妙。」
然後,又是一陣沉默。
諮商師想到個案的弟弟,他也是自殺而死,說不定他的父母會知道些什麼。
「據我所知,另一位令郎也是......是嗎?」
他們露出疑惑的表情,似乎聽不明白她在說什麼
「另一位?什麼意思?」瓊斯先生疑惑地說:「他是獨生子。」
這下子換諮商師弄不明白了。直到她想到個案描述「弟弟」的死因和個案上個月發生的事,個案和弟弟都喜歡音樂,她才發現其中的關聯性,提出了一個假設性的看法──他們是同一個人。
「對不起,您剛才是說令郎有在彈琴及創作嗎?」
「是的,雖然他現在已經不碰了,但他以前是非常熱愛音樂的。」
「令郎他是什麼時候開始不碰音樂的?」
「我記得沒錯的話,是高三那一年。」
「那是在我高中畢業那一年。」個案是這麼說的,他的「弟弟」就是在那時候自殺。
諮商師又問道:「那令郎在那時候有什麼異樣嗎?」
「沒有。」瓊斯先生回道:「那時候我們以為他想好好準備大學考試,所以屏除所有會影響他的事,包括音樂。」
「您支持令郎走音樂這條路嗎?」
「他做什麼我們都支持,」瓊斯先生說:「但我們會希望他先把大學學業完成。」
「我高三第三次模擬考沒考好。」
諮商師回到房間裡來,一坐下就問我高三時候的事。此時我已回復心情,心如止水。
「再過幾十天就要考試了,所以這時候失常是很危險的。」
我記得那時候班導的眼神,父母的訓話,還有同學的冷嘲熱諷。
「你不是校排第一嗎?」「怎麼這次考那麼差?」「你不是什麼都會?」我總是能聽到這些話。
也許他們是在開玩笑,但在我耳裡只是嘲笑和批評。
當我做得好,他們就稱讚,我失敗了,連一句安慰也沒有。我這才明白,一個人對待自己的態度和我的表現是呈正比的。所以我努力達成他們的期望,努力當一台完美無缺的電腦,活在一個只有1和0的世界。
「你的弟弟呢?他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?」諮商師又提起你。
「不停的創作,有時甚至會熬夜到三點。那好像是他唯一的樂趣。」
「那你知道他自殺的理由,或者他受到了什麼刺激嗎?」諮商師試探性地問道。
「不知道。但是我覺得他快被別人逼瘋了。」
「怎麼說?」
「其他人都一直逼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。有時他只想一個人創作,但卻推到台上,就像商品一樣被展示在眾人面前。」我說:「他一點都不想這樣,但為了他人好,他還是會忍氣吞聲去做。總有一天他會受不了的。」
「你覺得是因為這樣,他才決定結束的嗎?」
我低垂著頭,看著腳上穿著的墨綠色帆布鞋。我記得你也有雙一模一樣的。
「我不知道。」
「那你知道......」諮商師遲疑了,但隨後便開口:「......你知道你沒有弟弟嗎?」
我猛然抬起頭,試圖理解她剛剛說了什麼。我怎麼可能沒有弟弟,否則我的記憶裡怎麼會有這麼一個人?
諮商師看到我的反應,輕輕嘆了口氣,說:「我有個猜測......」
我的腦中一片空白,雙眼注視諮商師的瞳孔,想從其中找出一絲說謊的痕跡。我才不管她有什麼猜測,我只想釐清她剛剛到底說了什麼。
諮商師起身繞過她所坐的沙發,走向牆邊的書架,從那一排排的書中挑出一本,然後又坐回原位。
「社會心理學裡有一種自我概念,大致可分為現實自我(Actual self) 和理想自我 (Ideal self)兩種。其中現實自我為人們自身在社會、家庭和工作等領域中的角色,而理想自我是人們渇望追求的自我形象。」諮商師把手上的《社會心理學》遞到我面前,看我沒什麼反應就把它放在我前方的桌面上。接著她說:「如果沒錯的話,你的弟弟應該就是你幻想出來理想自我的形象。」
我不發一語。「她一定是在開玩笑。」我心裡這麼想。
「你應該很想當一名音樂創作者,我是說以其作為職業。所以,你幻想出的弟弟便是如此。」諮商師拿起桌上已經冷掉的咖啡,她啜飲一口後繼續說:「而這個弟弟出現的時間,你也可能不清楚,但至少知道他的消失和你放棄音樂的時間點是相符的。」
你真的不存在嗎?我的弟弟?
「誘發你弟弟消失的原因應該就是那一次考試。」
諮商師看我還是沒反應,她就引導我回想童年的記憶,回顧那段被埋藏在腦海深處的日子。
在記憶裡,我發現我在公園裡奔跑,然後在夕陽下和母親一起走路回家。我好開心,希望每天都能去公園裡玩。可是我沒發現弟弟的身影。或許那時我還沒有弟弟。
另一個畫面裡,我坐在鋼琴前,台下坐著評審和觀眾。我感覺得到心臟正猛烈的撞擊胸骨,還有無限的壓力壓在我肩上。我好討厭這樣的感覺。終於結束演奏了,我站到台前鞠躬下台,然後又站上台領獎,我努力搜索著家人的身影。我找到了,但是只有兩個人,沒有弟弟。
我懂了。其實,我們是一樣的,正如同十進位裡的二等於二進位裡的一零。看似遙不可及,但實際上是相等的。
所有真相湧上心頭,包括我所經歷的所有和痛苦。
「你發現了嗎?」
我點點頭。
「那什麼刺激你而有了尋死的念頭?你能說出來嗎?說出來會好過一點。」
不知為何我笑了,但我是發自內心的笑。不是我偽裝的。
「妳知道有時候要笑出來是很累的嗎?」
諮商師聽著我的一言一句。
「妳知道我是為別人而活嗎?」我身體往前傾,盯著諮商師說:「妳知道有時候......人無法自己做決定,人的選擇全被他人影響嗎?」
「你覺得自己沒有自由?」
「他們有時不會在乎什麼是我想要,什麼是我不想要的。」
「你有試著說出來嗎?」
「那妳覺得為什麼我弟弟會選擇自殺?他也是一部份的我不是嗎?」我笑著說:「如果一群人希望自己那麼做,那我不是就該去那麼做嗎?如果要從中選一個,我不是就該成為一個所有人都期待的人嗎?」
我看著腳上的鞋,說:「但我發現,就算他死了,一切都不會改變。」
不論我待在現實,還是逃向理想,背後仍有無數股壓力及沉重的期望向我席捲而來。
諮商師沉默不語。
「我累了,」我沒了笑容,我冷冷地說:「我只想要平靜,一點點就夠了。」
過了一個十年,我仍活在只有1和0的世界裡。
我站起來,準備離開這間喚起我真實記憶的房間。
「等等......!」諮商師叫著。
我走過櫃台,走下診所的樓梯。掛在門上的鈴鐺正叮叮地響。
我戴上帽子,淋著雨,漫步在人行道上,不知道哪裡是我的歸屬。周圍都變得緩慢了,而我的臉上掛著水珠。
氣溫如此冰冷,但我的手掌卻是溫熱的。一抹又一抹的紅霞在被擾動的水波中擴散。
我感到越來越冷,也越來越睏。
我好想念過往的自己。但我從未變過。2=1 0,十年過去了,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改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