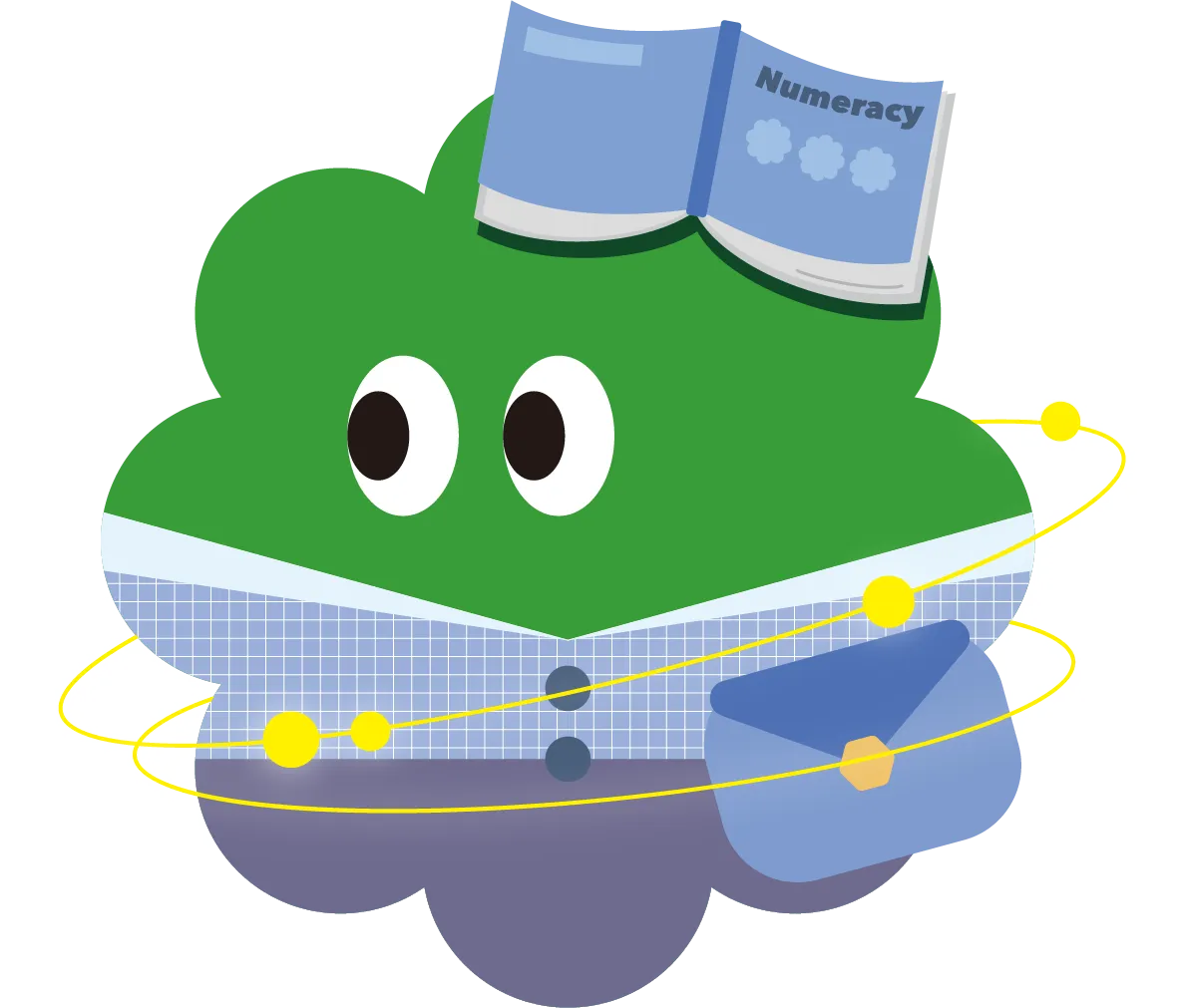作者 卡羿德勞 / 竹科實中
二十九歲的德˙費馬,寫了一封信,寄給了他的摯友:馬蘭˙梅森。上頭寫著:「我和你所剩的,差不多了。」梅森不解,費馬也沒多做解釋,關於他的愛情,他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。
那時的費馬,正身陷在一段熱戀裡,那名女子口中,有著濃濃的法國腔調,或許還摻雜著些淡淡菸草味。那樣子瀟灑的鄉村女孩氣息,沒有一點學院氣的女子,卻令他留神。
法國南部杜魯斯是個陽光明媚的小鎮。靠近庇里牛斯山的小山丘上,那是費馬屋子的所在地,夏天的陽光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反射了過來,碎碎的光透進了費馬的房間。他躺在床上,看著那如波紋般的光在天花板上舞動著,嘴裡念念有詞。
「真是不敢相信。」
他戀愛了。一個成年男子,懷著一個發光發熱的夢想,卻被一個在酒吧認識的女孩給深深迷住了。在這世上能夠讓他廢寢忘食的事有兩個,一個是數學,另一個,則是他深愛的女人。一個晴天假日的下午,費馬懶洋洋地躺著。
他盯著書桌上擺著的信,剛剛已經拆開來看過了,梅森不懂他前封信裡的意思,想請教這位數學天才究竟想說些甚麼。
「愛情好像是研究數學,你越想要得到,就越發現到它的深奧。」他眼睛直直地看著天花板說。
他坐起身子,翻身下了床,走到書桌前提筆在一張空白的紙上寫下: 「若p是質數,a是與p互質的整數,則a的p減一次方和p同餘。關於愛情,你和我一樣地失敗。」他不忘記在信紙底部畫上一個微笑,這微笑像是一個剛初戀的男子,對於浪漫的詮釋。
他現在對於數學已經失去熱情了,不,應該說他遇見了令他更充滿熱情的事物。他渴望,他想要,那樣地想要,他想要知道,那難以詢問卻得以輕易回答的問題,所求為何?
「我想要…知道那女人的姓名。」他小聲地說。
他站起身,披上了外衣,將信放進信封,又將信封封好蠟後,出了門,往鎮中心走去。
他來到了派信所,付了五十便士,將信寄了出去。回過神來,他已經走在回家的路上了。
突然,一個熟悉的招牌出現在他面前--「紅磚酒館」。就是這間店,他遇見那名女子的地方。他很想要走進去賭一把,但他討厭期待落空的感覺,這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常常發生,在以為要完美證明某個公式的途中,發現前面有計算錯誤,導致要從頭來過。與其失望落空,他寧可沒有發生過。
又因為,他害怕的是,那女人根本對他沒好感,對他沒印象,甚至討厭他。為了不要讓自已受傷,有時逃避一切是最好的選擇。
沒錯,費馬為了逃避一切,所以他進了酒館,點了杯啤酒,想要藉著醉酒忘了那個女人。
可惜事情沒有這麼順利,就在大鍵琴琴鍵開始跳動的那瞬間,酒館舞台上的女人,正用著她那濃濃的法國腔,唱著一首情歌。她,正看著費馬,費馬也看著他,兩人相視,空氣中透露著一絲未說出口的話語。
音樂休止,那女人鞠了個躬,台下觀眾喝采,也包括費馬。他身體不自主地朝著那女人走去,那女人也向他走來。兩人站到彼此的面前,互相看了看,費馬露出了驚喜的表情,而女人則是露出了靦腆的笑容。
「我們在哪裡見過嗎?」那女人問。
「不,並沒有。」費馬用著顫抖的聲音回答。
「那你為何一直看著我?」那女人挑逗似地問。
費馬低下頭,臉頰稍稍有點紅潤,開始漸漸燙了起來。
「因為……你唱歌很好聽。」費馬答道。
「嗯,知道了謝謝你。」
這是費馬第一次和她對話,他興奮地心臟怦怦跳。他想了解她,想要進而認識她,他開口問她。
「請問芳名。」他試著保持鎮定地說。
「嗯…我還沒打算告訴你。」那女人托著下巴回答。
「為甚麼呢?」費馬不解地問道。
「我已經想好了要怎麼回答你,但是現在沒有這麼多的時間。」
雖然他並不知道這個女人在說甚麼,但他認為這句話十分的美麗,像是一場戀情的開始,像是她對於自己愛慕的回應。
當天,費馬依著夜色奔跑在路上,帶著一些酒意,一路跑回家。他開心地跑著,不為了別的,他不想要被分離的感傷追上。回到家中,他躺在床鋪上,細細地思索著今天的機遇。她的歌聲還縈繞在他的耳際,她的神情還停留在他的腦海,她那句話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中。深深地,心臟似乎跳動的有點深刻。
不擅言詞的他,試著把今天的事記錄下來。他坐到桌前,思考著該如何下筆,這時字母對他來說是一種難以駕馭的事物。不知道要怎麼形容才能完美詮釋今天的夢幻禮遇。
最後,他在紙上寫下了畢氏定理,在旁註釋道: 「兩次我和她的遇見,形成了我們。」費馬將紙對折,夾進了他的數學計算本裡,像是珍寶一般地收藏。
後來,費馬經常在每天早晨徒步走到城鎮中心,說是去鎮上的麵包店買剛出爐的麵包。但是在買完麵包後,總是會繞去「紅磚酒館」去看那女人的表演,總是會在她表演完和她愉快地聊天,分享著他的生活,這同時也是他的夢,如夢一樣地生活。他從不和她解釋他這樣做的理由,就像那女人從不提及她的姓名。
他們會一起喝一杯酒,相互微笑地揮手告別。但這一天,那女人有事情必須先行離去,留下費馬一人,他不知道要做些甚麼才是。他決定去離鎮中心不遠處的小林子裡散步。現在是秋天,法國當地的秋天並不是個令人感到悲傷的憂鬱季節,而是個和煦陽光伴著涼快微風的日子。
費馬想起當初認識那女人的夏天,頭頂還是個豔陽高照的天。如今已經是個微微涼風吹拂之時,這樣的季節,多想有個人能依偎在身旁。他希望能和她更靠近,能慢慢地成為更深層的關係,但那女人卻像是有意地繞開他,漸漸地越來越遠。
當天晚上,費馬回到家中拿著筆和圓規在紙上畫來畫去,他從兩端一邊朝著反向畫圓,一邊縮小圓規的半徑,最後剛好相遇在一點。像是隻蝸牛的外殼,又像是遙遠東方的圖騰。他為這個圖形附上了一句解釋:「原本不相關的兩人,即使要繞遠路抑或是轉圈,也能夠交在原點。」突然間,他來了興致,他想要知道這個圖形背後的公式,該怎麼樣才能量化他和那女人間的故事。他興致勃勃地畫著座標軸,設了好幾個座標,列了一行行式子,使勁地算了起來。
曙光穿過了牆上的窗,他站起身子,伸展了一下。這距離他上次站起來,已經過了兩天又十五小時了。他不是靠著天賦來「發明」數學的,是靠著對於數學的熱愛,以及堅強的毅力來讓他「發現」數學。他將他的計算過程精簡成為一個公式,他把這個螺線以他命名,並把他為這圖形的附註,他的浪漫,一同寫在了信紙上,要寄給他的好友梅森。
他披上了外衣,將信放進信封,又將信封封好蠟後,走出了門,往鎮中心走去。又到了派信所,付了五十便士,將信寄了出去。回過神來,他才驚覺。他已經將近三天不眠不休,甚麼都沒有吃,就這樣子過了三天。這三天沒去找那個女子,不知道她會不會很錯愕。
身為一個數學狂熱者,他這樣是追求他的興趣﹔但身為一個戀愛中的男子,這是萬萬不可的。他焦急地走到了紅磚酒吧,還沒進去,就透過店面的窗戶看到了那名女子。正當他想推門進去時,他又看到了她身旁坐著一個男人,那名男人的親密舉動和有說有笑的嘴臉,讓他很不是滋味。他突然了解到:對他而言,那女人或許是他一生中的摯愛。但對那個女人而言,他只是一個生活中的過客,一個平淡小鎮人生中的刺激罷了。
於是他轉身離去,這次他逃避了,他離開了酒館,因為他沒辦法安穩地走入溫柔鄉,也就大步地離開,往家的方向回去。
又是一個三天,又是連續三天沒有進食。費馬就一直躺在床上,偶爾起來上個廁所,便又倒回床上。像是行屍走肉,又像是一坨會呼吸的肉塊,靜靜地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。
突然,外頭傳來急促地敲門聲。費馬有氣無力地問道:
「是誰……」
「是我!」
外頭傳來一股熟悉的腔調,是那名女子。因為連連不見他好幾天,擔心他出了事,便趕來他的住所探望。不料,費馬並沒打算應門。
「你出了甚麼事嗎?」那女人問到。
「沒什麼事情。」費馬隔著門回答。
「那你為何最近都不來找我了?」
「有事在身。」
「甚麼事情,我可以知道嗎?」那女人有些好奇地問。
「你叫甚麼名字。」費馬問。
這時那名女子猶豫了一下,想了想還是決定回答他。
「安妮。」
「安妮…安妮……」費馬小聲地複述了幾次,若有所思地唸著她的名字。
「還真是好聽呢。」
「你還有什麼事情想問嗎?好久沒有聊天了。」安妮低頭看了看地板並不髒,拍了拍地板,就坐了下去。
「那個男人是誰?」
這時氣氛凝結了許久,兩人都沒有說話,連遠處的鳥叫聲都聽得一清二楚,彷彿氣溫低於了絕對溫度,冷的兩人都無話可說。安妮並不想回答,卻又很想和他解釋。費馬大概心裡有數,無力地說道。
「沒關係,其實妳…」
「他是我未婚夫。」
還沒等費馬說完,安妮就打了岔,說出了這駭人的消息。一時間,費馬難以接受,但其實心裡早已預演過好幾次這種情節了。氣氛又是一陣尷尬,直到安妮再次開口。
「很抱歉,費馬,遇見你不久前,領主剛幫我決定好了這門婚事,起初我是千百個不願意,這時你又正好闖入了我的生活,我萌生了想和你一同逃亡的念頭。但是我漸漸了解了我的未婚夫,變得沒有那麼想要逃走了。他人很好,就跟你一樣。」
費馬像是失了神似地看著地板,眼神空洞,腦海一片空白。這樣子的劇情,就好像告白前就遭到拒絕似的,心宛如刀割,難過無可比擬。
「謝謝,你回去吧。」費馬淡淡地說道,同時又挺起了靠在門板上的身子,直直地倒在床上。
安妮十分不忍心,但是費馬並沒有想要答理她的意思,她便起身離去。離去時不忘回頭看著門,小小聲地說。
「對不起。」便略帶難過地回去了,離開了費馬的屋子,也同時離開了費馬的生活中,就這樣輕輕地離去了。
留下了費馬一人,仍然倒在床上,他不知道他做錯了甚麼,是他愛上了一個有婚約的女子?還是他根本就不該擁有愛情?這問題讓他困擾許久。最後他決定離去,離開這個現在只要看著,就令他厭煩的小鎮。
一年後的冬天,在費馬爸爸的屋中,費馬正在書桌前發呆,呆呆地看著外頭的路人從窗前走過。房裡溫度偏低,可能是因為外頭在飄雪的緣故,冷空氣不斷地透過窗子鑽入。
這時有個女子走進店裡,要取走之前訂製的皮革。那個女生抬起頭,費馬不禁嚇了一跳。
「安妮!你怎麼在這裡。」
「費馬!」
安妮也嚇了一跳,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巧遇十分訝異。費馬把她留了下來,和她聊聊他離開後的事。
「你和你先生怎麼樣了。」
「很好,我們也搬到城裡來了。」
「你們適應的還順利嗎?」
「還可以,我在附近的酒吧駐唱。嗯…如果有空的話你可以去看。」
費馬禮貌地點了點頭,安妮則站了起來。
「抱歉,我等等還有事,先走一步了。」
「好的。」
當天晚上,費馬來到了安妮口中的酒吧,點了一杯啤酒,找了個位子坐了下來。就在快要喝盡的時候,舞台上傳來了一個熟悉的歌聲,是安妮。她的嗓音還是那樣地動人,還是有著濃濃的法國腔調,聲音還是那樣的有魅力。
費馬還是一心愛著她,但是她卻沒有辦法和他有更深一層的關係了。就在歌曲盡了、人將散去之時,安妮走下舞台,尋找著費馬的身影,不過她沒有找著。他留下的啤酒杯下,墊著一張信紙,從字跡可以看出那是費馬所留的信。
此時的費馬已經回到家中,他一直都知道,他所愛著的,從來就不是那個名為安妮的女人。他所愛的,是個更深層、更值得他所愛的事。他願意為她付出時間,願意把餘生都獻給她﹔他可以為她拚命地闖蕩,在寂靜的夜裡與她安靜地對話。他並不知道這是不是他的初戀,他只知道這會是最後一次的戀愛。
他坐到書桌前,拿出了信紙,在紙上寫下一個方程式,並又在旁邊解釋道:「關於此,我確信我發現一種美妙的證法,可惜這裡的空白處太小,寫不下。」當他想要將信紙對折時,他遲疑了一會兒,又把信紙打開,補充道:「不管經歷過幾次的我,和幾次的你,結果都不會是我們。」他這才安心地將信摺好放進信封裡,又將信封封好蠟後,走出了門。
他感受到一股溫暖從他胸口處溢出,拿出來一看,是那個即將寄出的信封。他看了看,笑了笑,這是就是他此生的摯愛。他留給安妮的不過就只是一句道別,畢竟他要將他的文筆和時間都留給正確的人。
「她才是我今生今世的摯愛啊,我願意把時間都給她,哪怕我有天死了,也想活在她的回憶中。」
有件事情值得你付出所有,那便是愛;有個人值得你對抗一切困難,那就是愛。他將信交給了派信所,那是他對於他真實戀情的誓言,這個瞬間,他讓未來的許多男人,都因而陷入了相同的熱戀。
過了許多年,後人幫他在信裡寫到的這個公式取了個很美的名字,叫做「費馬最後定理」,那不僅僅是一個數學公式,她是一段愛情故事,講述著費馬的初戀,她是一個他對於他愛人的描述;更是費馬前半段人生的大綱。
這個她,不僅僅讓費馬將往日餘生都獻給她,也讓後來的數學巨擘們,一個個紛紛獻上他們的人生、他們的未來。有些人因為她而有所成就,也有些人因為她而終生沒有工作。她就是費馬終生的摯愛,畢生的情人,也是他最後的真愛。是的,親愛的,她就是你我皆知的--「數學」,使一群人類從浪漫到瘋狂的愛情結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