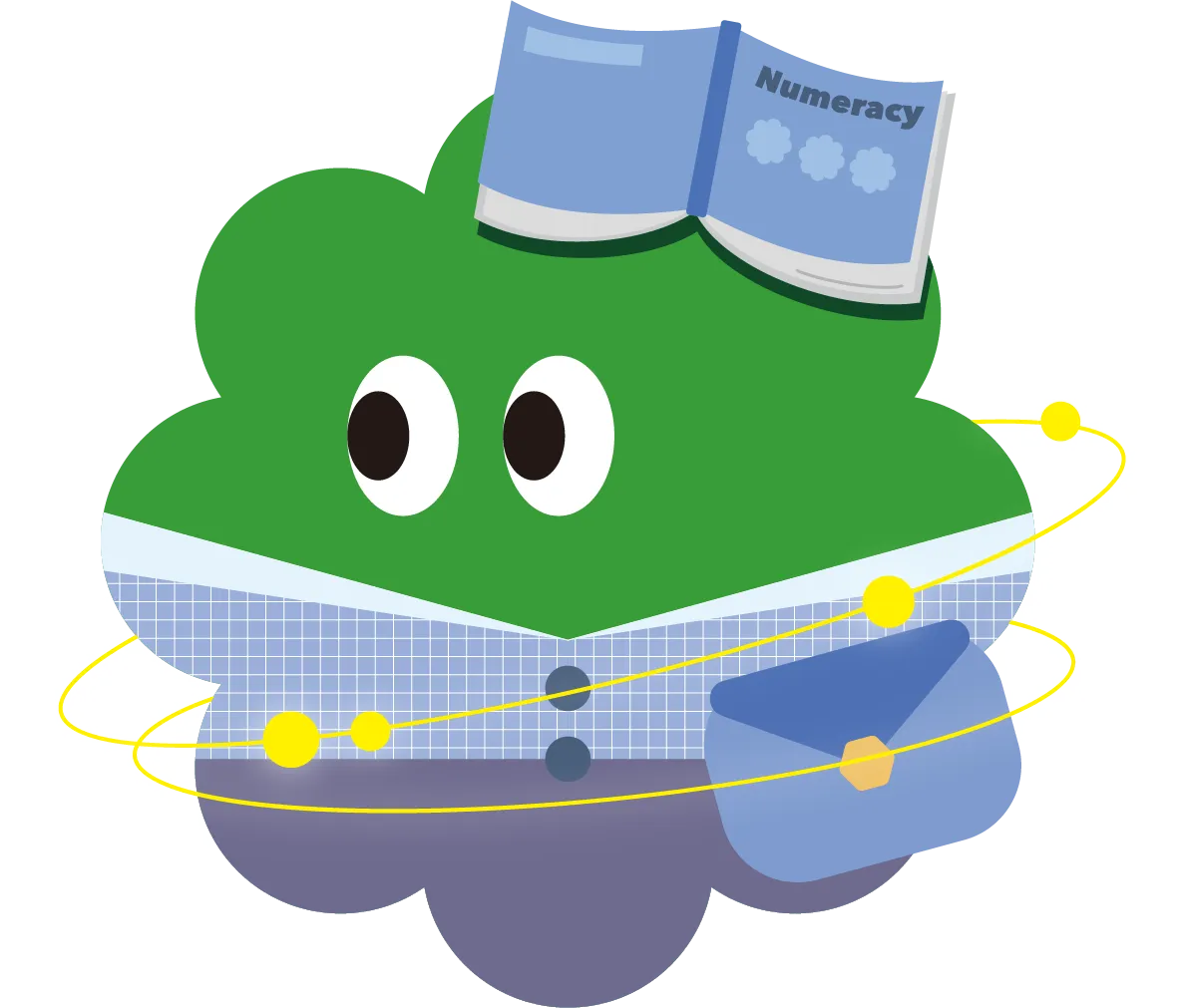作者 林佩妤 / 新竹女中
「怎麼可能!」
「真的啊!不然妳告訴我,二的多少次方能等於或小於零?」
「可是……你說這兩條線會越來越靠近,那一直畫下去,總有一天它們一定會相交的啊!」
我看著瑤,突然失語。
瑤認真思考時會咬手指,像剛長牙的嬰兒輕輕含住拇指,或把指尖擱在兩排牙齒之間。如果能留下發紅的淺淺牙印,那便是道難題了。她的一雙淡眉也會蹙起,不太明顯地,成兩道生動的流線。我的目光停駐在她身上,總會不知不覺失神。
幸好她總要想很久,足夠我失神,聚攏注意力,又再次失神。
有八成的機率,她會帶著迷茫的眼神抬頭,用鼓起的腮幫子示意求救,或懊惱地嚷嚷:「吼!數學為什麼這麼難?」
而我總會安撫地一笑,拾起她摔在桌上的鉛筆在指間迴個圈,謄上一次比一次更詳盡的算式,機率是一。
瑤的數學極差,彷彿大腦某一塊硬是被挖空;不論她如何在考前纏著我問遍每一題,我總感覺她抗拒臣服於數理世界的一切規則。
「其實我到現在還是不能接受假分數。」某次上課前,我在黑板上抄寫算式,她突然在身後悠悠說道。
「這不是國小就學過了嗎?」我往旁邊跨一步,畫起小學課本上最常見的大餅和賓士標誌,「有四塊三分之一的餅,就是三分之四啊。」
「三份裡的四份,這句話本身就太不合邏輯了吧!」她伸出右手在黑板上敲了敲,「你看,你明明就畫了六份,為什麼分母是三?」
也不等我回話,瑤向著發愣的我燦然一笑,轉身一蹦一跳地走了。
她向數學表達厭惡的方式,就是對那些冷硬的符號和圖形加諸各種想像,化了裝才願意勉強嚥下。她說√是家,所有數在裡頭都會變得鬆懈懶散,戰鬥值大大降低;她說橢圓方程式是圓融共好的最佳典範,不像雙曲線,相互減損斤斤計較,只落得兩個相互遠離的背影。
而我喜歡數學,本質上的數學。喜歡它的確定和絕對,喜歡它總有固定的邏輯可循,幾行算式就能把龐雜的問題分崩離析,總有肯定的簡單解答。畢竟,生活在這世上,我們得面對的不可解難題已經夠多了。
比如,身為理應相斥的同性,為什麼我總在瑤低頭研究我的筆跡而髮香緩慢流瀉的時刻,下意識地挨近?
「教我這題好不好?」好長一段時間,我和瑤的對話都是這樣起頭的。
她會把攤開的書啪地橫在我面前,雖然是問句卻說成肯定的語氣。瑤不用請求,她是那樣有本錢把任性當作可愛,想要什麼便不曾失望的女生。
我習慣寫下解題步驟再慢慢解釋,剛開始,我們之間總要先橫亙一段靜默,只有鉛筆在紙上起舞的沙沙聲。沒多久,瑤便開始補起這塊空白。她喜歡說話,從天氣到家裡的小狗到補習班打工的大哥哥,帶著笑的語調總是上揚,像對這世界有耗不盡的驚喜和熱情。
我喜歡聽,只要微笑著點點頭,或虛應幾聲,她清脆的聲音就會如關不上閘門的流水。瑤是迪士尼動畫裡會推開窗戶向鳥兒唱歌的公主,聽著她描摹所見,我竟也浸染了一點那明亮得不真實的陽光。
偶爾,我們甚至就這樣走出教室,去找那朵初綻的小花,或福利社新上架的糖果。未解的數學習題被擱在書桌一角,孤伶伶地,彷彿從未有人為此而來。
青春的確不是為此而來。
「走啦!」後來,瑤總想把我拉出書本的世界。我慣於蜷縮在木桌椅之間,呼吸教室裡悶滯的,溫暖溽濕的空氣;可是瑤是生活在天空下的,不會容許一點黴菌孳生。
「等一下,等我把這題算出來……」
「快點!我要和別人走了喔!」
每一次被扔下的總是課本,我向等在門口的她走去,只是相視便咧嘴笑了起來。
瑤的確是我生命裡的指數函數,踩著不起眼的姿態出場,渾然不覺間已經站上座標的最頂端。
跑步時,她的高馬尾一晃一晃,彷彿是為了被陽光鑲成耀眼的金色而紮起的;白色襯衫在風裡鼓動,像纖薄的,只屬於天使的翅膀。比起跨步更像是輕盈的跳躍,我時常覺得她下一秒就要起飛。
「好了啦!很累欸。」氣喘吁吁的我飛不動,我是笨重的凡人。
到底為什麼要出來跑步啊?我總來不及問。
只要一停下腳步,瑤就會握住我的手腕,拖著我繼續前行。一旦被那冰涼的手指圈住,感覺自己的體溫漸漸注入那緊貼著的,軟膩如脂的肌膚,我就會瞬間喪失組織語言的能力。
是她的手太冰了。我告訴自己。
是她太特別,我才記住了所有細節。
她是漂亮的黃金分割數列,數學家總忍不住多看兩眼,僅此而已。
天平的失衡只是一瞬間的事,每次實驗的最後,讓一端沉沉下墜的,都是最小的那顆砝碼。
這道理我懂,只是一直未曾意識,自己早就踩在一個擁抱便能摧毀的薄弱平衡上。
那天,發完段考考卷的下課,才從座位上起身,一雙手臂便從背後牢牢圈住了我。那氣味——帶花香的清甜潤髮乳摻雜衣服上淡淡肥皂香,和自腰側滲透的微涼體溫,令我動彈不得,是瑤。四肢突然都灌了鉛似的,僵硬得不聽使喚,我挺直背脊,連呼吸都小心翼翼。
「怎麼了?」幾秒後我才記起如何開口,很輕很輕,自己也差點沒聽見。
她沒有回答,連個動作也沒有,像掛在背上的破布娃娃。
我心虛地東張西望,當然沒有對上誰的目光。女孩之間的肢體接觸大家都見慣了,沒有人會發現我越發滾燙的雙頰,和一陣快過一陣,像要撞破胸口的心跳。
除了瑤。
倏地一驚,我急欲掙脫,就怕被她看穿自己的不自然;握住纖巧得彷彿只剩骨頭的手臂後,卻又不忍心推開了。未完的動作打住,無所適從,最後只是盡可能溫柔地在那手腕上拍了拍。
瑤仍然一點反應也沒有。
緊張逐漸消散,疑惑不安隨之湧上。那個總笑得像冬陽的女孩怎麼了?什麼也不說到底是怎樣的心情?她……在哭嗎?
心緊緊揪起,莫名地發脹發疼。
是數學又考差了吧!雜亂的思緒在腦海喧騰。等等我該怎麼做,該鼓勵還是安慰,還是若無其事說個笑話?噢該死我最不會說笑話了,是說我們該一直僵在這裡嗎……
瑤一鬆開手,我馬上轉身,在那張臉上探尋。幸好,沒有淚痕,也沒有太沉的沮喪悲傷。
「有點對不起妳啊!」瞳孔盪著失落的漣漪,她噘起嘴,拉起我的手腕晃了晃,「妳花了好多時間教我,我還是考得這麼爛……」
懸起的心坐了趟雲霄飛車,我還沉浸在如釋重負的輕盈裡,想也不想便牽起她,淡淡的笑了,「沒關係,這樣也好啊。」
「什麼?」
望進她瞪大的眼睛,一陣寒意襲捲而來,我恍如在無盡的深淵裡下墜,萬劫不復。
這樣也好啊。
妳就會永遠需要我了。
日子是匆匆翻動的頁,滿街飄落的枯黃送走夏天,秋天也以遞增的步速走近又遠離。
但學生生活是恆定的常數,家,校園,補習班,三點一線。可以三步併作兩步,也可以繞進曲曲折折的小徑,終究去不了更遠的地方。
我可以有無數閃躲的藉口,無數蒼白的解釋,就是控制不了在人群兜兜轉轉後,總會回到瑤身邊的目光。
有時候,我慶幸自己擁有和她一樣的一頭長髮。那天生的偽裝足夠我肆無忌憚,一次次從名為友情的擁抱裡汲取她的氣息。像數學,多麼自然的,供我們肩挨著肩重疊視線的理由。
有時候,我也厭惡自己和她走進同一間廁所的權力。在她毫無保留的笑容裡,我總被罪惡感淹沒,確知自己就是小偷,無可自拔地偷嚐不該屬於我的甜。就像開始討厭數學,討厭一條曲線和直線的永遠不相及。
明擺在眼前的,是無論我前進多少步也無法跨越的距離,不可動搖而絕對,不為零。
「妳可以在一後面加無數個零,產生無限大的數,對吧?」瑤不太情願地點點頭,「那它的倒數,也就是把它放在分母,是不是就能產生無限小的數?這就是圖形和漸進線的距離。」
「可是如果畫成圖……」訊息音打斷她未完的話,即使瑤馬上拿起手機,螢幕亮起的那一瞬仍夠我看清了,是她的男朋友。
我擺擺手,「好啦不用藏了,妳去吧!」
瑤略帶歉意地笑了下,手上收拾的動作倒是很俐落。把書包甩上肩,她誇張地嘆了口氣,「我這輩子大概都搞不懂漸進線了。」
逆著光,她輕快的腳步舞成飛揚的剪影。一直那麼單純的直線世界啊!注定要遇見的人總會交集,而後再什麼也不考慮地遠離。
「這樣也好啊。」我喃喃自語。
「蛤?」
「沒事啦,掰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