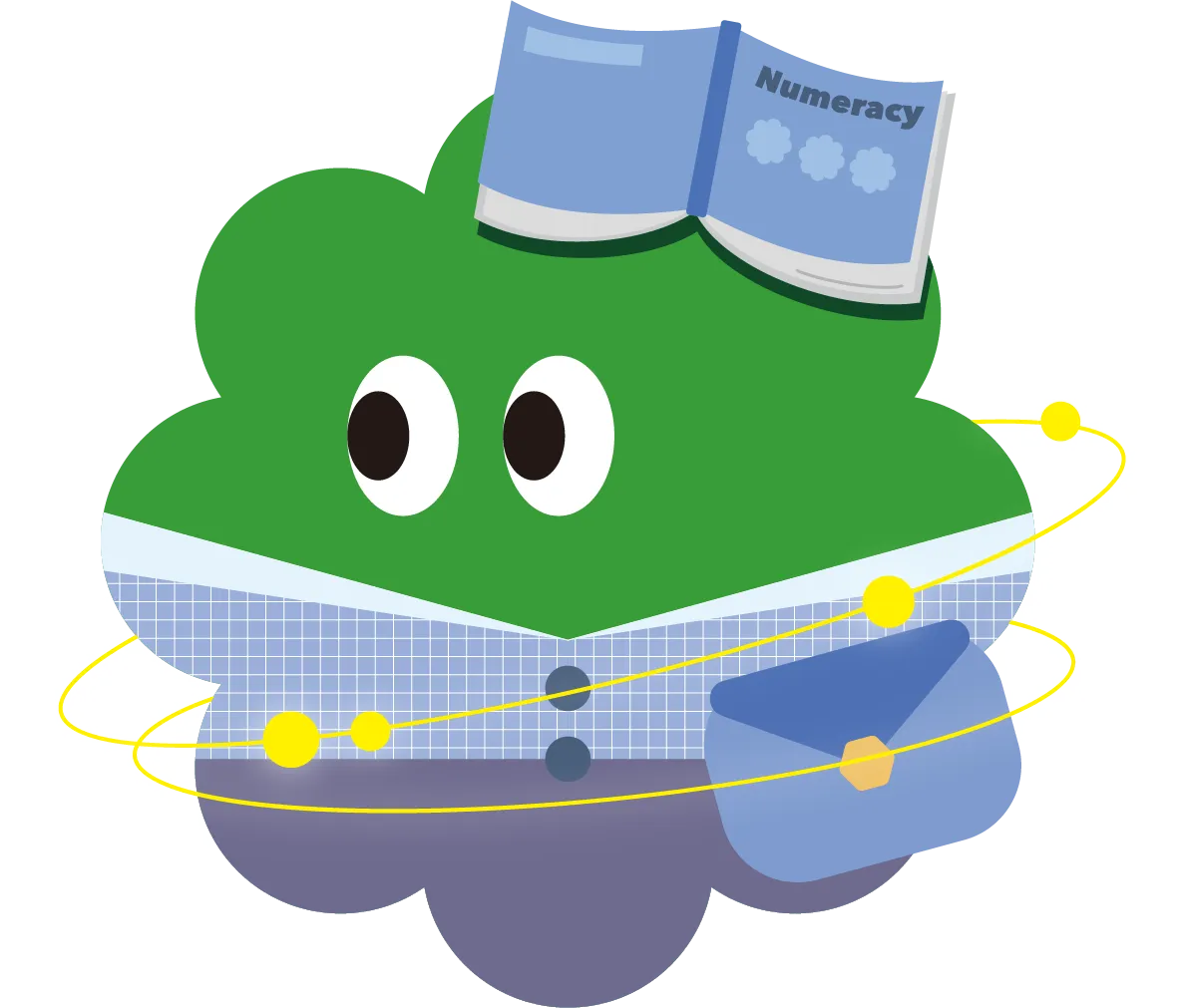作者 魏黛甄 / 嘉義市嘉義女中
沒有人想過,那些只在電影出現的災難,會有一天活生生的出現在人們面前。
至少蔡冠宇真的從來沒想過。
「各班緊鎖門窗、關上……嗡嗡嗡嘎咿!!!!!」突如其來的廣播,打亂了上課的節奏,斷訊的聲音,如同高亢的尖叫。
半信半疑的氣氛並沒有瀰漫太久,「碰碰碰碰碰!」一陣瘋狂的拍門聲,頓時令整個班級再無人敢吱聲。
「救救我啊!」門外的人撕心裂肺的喊著:「殭屍......有殭屍在追我!開門!快開門!」捶著門的手在玻璃板上砸出了血痕,緊接著映出一個圓敦的輪廓。這下開始用頭撞門了,有人露出不忍的神情。
「誰開了門?快把門關上!」老師忿然作色,急忙向前準備將門關上,不料,隔壁班的矮冬瓜已從門縫間擠了進來,跪倒在地上大口喘著氣。
矮冬瓜的衣服破爛成一塊不足以遮羞的破布,身上也有幾處不明的傷,最重的傷勢是脖子上的那道咬痕。
「同們、不對,同學們......都變成殭屍了......」他全身顫抖,頭上的汗不停滑落,說不出一個清晰完整的字句。
「有ㄌㄣˊ…有人跑進我們班,咬……」他還想講,但是,突然雙臂一軟,整個人癱軟在地上,雙眼無神,隨後又兩眼向上一翻,口吐白沫。
「啊──」有人遮住雙眼,有些人往教室後面退,發出微弱的驚叫。
矮冬瓜的球友阿鐵屏住呼吸,緩慢地察看倒下的「它」──
來不及了。
「它」從地上彈起來,狠狠咬住來人的脖子,雙眼仍是翻白眼的模樣,頭還呈現不自然的歪斜角度。
「啊──」尖叫聲震耳欲聾,每個人都互相推擠,「矮冬瓜」卻不停的攻擊同學。
鐵鏽般的血腥味漫延在教室裡,血液浸透課本,包含老師的、那些發抖的同學的,和那些已經開始互相攻擊的同學。
事情發生得太快,把蔡冠宇嚇得從椅子上跌下來,撲騰向門邊逃命。
殭屍、咬痕、感染。幾個字眼從他的腦海中飛快閃過,還沒能細想,一張扭曲的面孔逼近,強而有力又歪曲的手指緊抓著他的手臂,「滾開!」大概是腎上腺素激發,他用力甩開束縛,拿起教室後方的掃把,奮力將擋在門口的殭屍通通推開,一邊大吼著衝出教室。
「碰!」伴隨門打開的巨大聲響,在走廊另一頭遊蕩的感染者如潮水,發狂似的朝他奔湧而來。
他緊握手中的掃把胡亂揮舞,沿著走廊狂奔亂竄,望見了走廊的盡頭,就像看見了自己的盡頭。
緊貼著牆壁,他顫抖的手探著空教室的門把,瞪著四周的怪物。
「我不要......我不要變成這樣......」三雙糊滿腦漿的手一齊探來,蔡冠宇頭一縮,身旁的門突然打開,裡頭伸出一隻手抓住他的手臂,將他扯進教室裡。
「放開我──嗚啊啊啊啊!」教室內一片漆黑,一隻纖細但有力的手禁錮住他的身體,另一隻手則摀住他的嘴。
「噓,安靜點。」是一個冷靜的女聲。
「雖然他們理智上已經瘋狂的不像人類了,但還保有五感,唯一捨去的是痛覺,一旦他們發現你,會無所不用其極的感染你,即便斷手斷腳也無所謂。」
等到外面聲音漸弱,雙腿發軟、跌坐在地上的蔡冠宇熟悉了黑暗,勉強看清是誰及時救了他──一頭凌亂短髮的女生,正微微的掀開窗簾,用她銳利的眼神確認危機解除。
她嘆了一口氣,鬆開緊繃的雙臂,掏出手機。藉著手機的亮光,他才看得清楚,眼前的人看起來成熟又從容,大約二十幾歲,脖子上掛著條閃亮銀色的項鍊,不像是學生。
蔡冠宇愣了一下。「痾,謝謝你......救了我,但你是誰?」
她抬起頭,撥了一下頭髮。「嗯。」又有點彆扭的騷了搔頭,「我嗎?我是......痾......理化老師。」
「喔,我都不知道我們學校有這麼年輕的理化老師。」
「現在外面已經淪陷了。」她清了清喉嚨,像是在轉移話題。「在教室的人幾乎都被感染了吧,我們最好還是保持安靜,別被發現了,誰也沒想到殭屍竟然會撞破玻璃。」
蔡冠宇雙手猛然抓住女老師的肩膀。
「不會吧?你真的出去過嗎?你沒看到正常的人嗎?我能還活著我哥也該活著吧!他還欠我錢、要洗今天的碗、這週要遛狗,要……」
「勸你做好最壞的打算。」
「我不管!我要去高中部找他!」甩開腦中哥哥翻白眼、口吐白沫的畫面,他搖搖晃晃的起身。
「......」那女生像是在盤算甚麼,「好吧,樓梯間還有殭屍,等他們走遠了,我就跟你一起去找你哥。」
「喂!發甚麼呆啊?」被一包衛生紙無情砸中,將蔡冠宇從回憶拉了出來。
「北七喔──」他撿起地上的衛生紙。「我在想如果那時候沒有去你們班救你,你是不是還躲在櫃子裡發抖呢。」
「哼。」蔡冠均冷笑一聲。「我看如果沒有我,你早就撐不下去了吧,骨頭大概正被哪隻殭屍啃食吧。況且,別說你是來救我的,我還記著你當時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蠢樣呢。」
蔡冠均被救出來的過程驚險萬分。當時教室已無活物,躲在教室置物櫃的蔡冠均逃過死劫,那些濃黃赭紅的碎骨斷肢,現如今他們兄弟倆沒人想提。
短短幾天,遊蕩的喪屍佔據市中心,毀損的街道、破裂的玻璃櫥窗、空無一人的住家,不見人類文明的蹤跡。為了活下去,蔡氏兄弟與理化老師冒險離開學校,向城外移動。現在,三人暫時待在一棟三層樓的社會住宅裡避難。
「餘暉姐呢?」蔡冠宇往三樓窗外望去,內心感嘆這瘋狂的世界。
「曾老師出門找食物,這棟樓裡連水都沒有了。」
「她不是說別叫她老師嗎,都世界末日了,哪有人在乎這種事了。而且,為什麼不是你出去啊?她是女生耶!」
「女生?她可救了你一命,能力比你強多了,相比之下,我們兩個只是屁孩。」
「嘖。」蔡冠宇不滿的咂了嘴,之後就沒再說話。兄弟倆無言的坐在房間。
夕陽染紅大地,也染紅整座城市,整座城市籠罩在不祥的血色之光中。三天了,再不吃東西,恐怕只能等死。
房門被推開,兩盒披薩被丟在桌上。
「披薩店被翻過一輪,這兩個僅存的披薩是在烤箱裡找到的,可能不太熟,但這附近已經沒多少能吃的食物了,我們要好好平分這兩盒披薩,對了,沒有蕃茄醬和胡椒粉了。」說完,她打開披薩盒,是臘腸和夏威夷口味的。
「姐,別提蕃茄醬了。」蔡冠宇一時有些反胃。
「我們要怎麼分?」
「每個人都拿一樣的份量吧。」儘管很餓,但看著同樣飢餓的弟弟和剛歸於安全的老師,蔡冠均最後這麼說。
三人跪坐圍著矮桌,一時間對這兩盒珍貴的披薩無從下手。
「要分成幾份?」
「我來算算!」蔡冠宇自告奮勇的說。「假設每人一天吃四片──」
「你是白癡嗎?這種時候還吃四片?有得吃就該偷笑了吧。」蔡冠均無情的打斷,讓他十分不滿。
「我以前一餐都吃四片啊!讓步到一天吃四片已經不錯了吧!好吧──那每人一天兩片,三天就是六片,我們三個人──」
「總共十八片,也就是一盒披薩分成九片。」話又一次被打斷,要不是因為那人手上拿著刀,蔡冠宇實在無法忍下這口氣。
「痾,九片?這要怎麼切啊?」頓時房間內一片安靜。
「所以我說還是一天四片吧?」「閉嘴,這樣一盒要切十八片,不如剁碎披薩都比較快。」
房間再次陷入安靜。
「我知道了!」蔡冠宇靈光乍現,興奮的拍了一下手,起身從書桌上隨手拿了紙筆,一言不發的開始在紙上作畫。
在他一陣塗抹與思考過後,他甩了甩紙張,向兩人展示自己的豐功偉業。
稚嫩的筆跡描繪著歪七扭八的圖形,幸虧圖的旁邊有註釋,不然兩人對眼前的畫肯定是丈二金剛,摸不著頭緒。

「我之前看過日本的數學競賽,可以這樣分,每一塊都是三等份!我們一人一
份,自己再分配每天吃的量吧!」他興奮的搖晃手中的紙,覺得自己真是個天才。
「咳咳。」蔡冠宇打量了這四張圖,搖了搖頭。「先不論這是不是三等份,這
是實際上切得出來的嗎?還有,『削皮機』的『削』是刀字旁的『削』。」
再次被潑了一身冷水的蔡冠宇不服氣的急忙辯解。「那不是重點!這真的都是三等份!」
同心圓的圖,假設這三個圓的半徑分別是r、2r、3r,那麼黑色部分的面積就是,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披薩,畫線的面積和黑色的一樣,所以白色的部分也會是三分之一!」
「下面那張圖很好理解吧?半徑如果分別是√3、√6、√9,由內而外的面積就會是√3²π、√6²π-√3²π、√9²π-√6²π,通通都是3π!」「可是,這樣分到最外圈的人就只能吃餅皮了耶。」曾老師看著圖片、歪著頭說。
「右下角的圖,」蔡冠宇完全不理會旁人,自顧自的繼續說。「先切成四等份,每人分到一份,再把多出來的一份繼續切成四等份,重複步驟無限次,就能趨近於將整個披薩分成三等份了──啊!好痛──」蔡冠均聽不下去這些荒謬的切法,一拳落在他的頭上。
「夠了,重複無限次要切到甚麼時候啊?你不能想點更實際的方法嗎?水果削皮機的方法就更離譜了,直接把披薩榨成汁、倒成三杯都比較實際。」蔡冠均放下手上的刀,一把搶過蔡冠宇手上的鉛筆,又拿了一張新的紙。
俐落的線條畫在紙上,不像蔡冠宇,蔡冠均過沒多久就畫好了圖,字跡也比弟弟整齊許多。

「左邊這張圖是把直徑分成四等份,再按照我畫的線切披薩,就能切出簡單又完美的三等份了。」
「可是你怎麼知道每片披薩的圓心角都會是120度呢?」蔡冠宇抽走他手上的紙,仔細盯著簡潔有力的圖片。
手上的紙又再度被抽走。蔡冠均用鉛筆框起畫斜線的扇形裡的三角形。
「學過邊長1:√3:2的三角形嗎?」「嗯,上學期學過了。」
那三角形被畫上了底邊的高,還不忘加上垂直符號。「高是一半的半徑,斜邊是半徑──」
「哦,我知道!這底邊是√3倍的半徑。」
「那邊長1:√3:2的三角形有甚麼性質?」
「我想想......啊!角度分別是30、60、90度!」
「對,所以上面這個角是60度,兩個三角形合起來就是120度。」
蔡冠宇恍然大悟,又急忙指向紙上右邊的圖。「那這個呢?」
「簡單來說,只要刀數是大於2的偶數,隨便選一個點作為中心點來切,每刀之間的角度又相同,那麼我畫的區塊面積就會相同。」
「披薩定理。」曾老師補充。
蔡同學歪著頭,顯然還是難以理解。
突然,一直沉默的曾餘暉拿走了筆。
「那如果這樣呢。」她又畫了一個圓,撈出項鍊,照著樣式在紙上作畫。

兄弟兩人對著老師的圖目瞪口呆,同時說出:「這是三等份?」
「怎麼樣?六芒星很美吧!」她拎起脖子上的項鍊,銀色的六芒星墜飾反射著白色日光燈,在她的手中熠熠生輝。
「真的好漂亮啊,但要怎麼證明這是三等份?」蔡冠宇望著閃亮的小吊飾出了神,急忙將話題拉回正軌。
她又低頭畫了一張圖,另外兩人湊在她的身旁。

「咕嚕──」不知是誰的肚子發出抗議的聲音,打斷了三人沉默盯著紙張的時光。
「噗──哈哈哈!」蔡冠宇忍不住笑出聲來,他雀躍的站起身。「我宣布──本次披薩切割大賽由餘暉姐獲勝!」
「不是吧,我的切法比較實用吧!」蔡冠均難得顯露出不服氣的一面,兄弟倆又再度開始拌嘴,讓奪冠的人忍俊不禁。
「呵呵,別鬧了,肚子都餓壞了,趕快來切披薩吧。」
最後,蔡冠均選擇用三片圓心角120度的扇形的方式切完兩盒披薩,但也沒有實際將直徑分為四等份,只是憑藉第六感,爽快的在披薩上落下三刀。
另外兩人看著分好的披薩,又是一陣爆笑。
「哈哈哈──這真是太荒唐了,討論了這麼久,還是用這麼普通的方式解決了──」說實話,就連蔡冠均也覺得荒唐,忍不住一起加入歡笑的行列。
在疫情爆發的第三天晚上,三人暫時忘記自己身在這頹垣敗壁的城市。橫屍遍野的街上沒有自己、尺椽片瓦的屋內還能有笑聲,一起解決了披薩問題,說不定他們能一起解決更大的難題。
翌日早晨,陽光如金色瀑布傾瀉在房間的每個角落,但少了一個人。
「喂!快醒醒!」蔡冠均蜷曲的身體抖了一下,驚醒。
昨日享用披薩的位置變了樣,畫著披薩圖形的紙張血跡斑駁,剩餘的披薩散落一地,矮桌上的東西全翻倒在地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地板上從房間延伸至樓梯的血跡。
蔡冠均探向窗外,那熟悉又扭曲的身體倒臥在大街上,心情複雜的將窗簾拉上。
蔡冠宇走了過來遞給他在桌上發現的東西:一張報紙、一張從日曆紙寫的字條,以及一條沾血的六芒星項鍊和兩支裝有透明液體的針筒。
報紙是幾個月前的,照片上是一頭烏黑長髮的女科學家拿著獎盃,銳利的眼神嶄露自信,醒目的標題寫著「賀!女性科學家曾暉妤榮獲……」後面的字被血污遮蓋了。
字條上,一筆一劃、刻得用力地字跡寫著:「我不是理化老師,我是外洩殭屍病毒的罪魁禍首,第一時間逃到研究室附近學校的混蛋。政府委託我非法研究這個病毒作為生化武器,對不起…什麼餘暉,我根本把世界推向末日。我是沒用的曾暉妤…」
報紙下方是文藝小專欄,介紹的是六芒星的民族意義,幾個尚可辨認的鉛字印著「生命輪迴、自由、希望、保護」。後面被加上幾個潦草的鉛筆字:「研究室、密碼」。
豆大的淚珠落在紙上,雙肩不受控制的顫抖
「我想我們昨天不該那麼快樂。」蔡冠宇的情緒十分複雜。
「我恨她。」蔡冠均想起教室裡同學們的遺骸、生不如死的日子,眼淚滑了下來。
「但他救了我。」蔡冠宇站起來。
「也救了我們。」並指向掉落的、被踩爛的披薩。
「或許她昨天就在暗示我們甚麼了。」
「走吧,去研究室,死也要去。揭開一切的源頭。」
蔡冠宇緊握手中的銀色項鍊,那充滿悲劇又散發餘暉的六芒星。